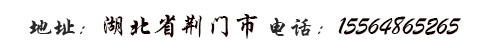九个大衾岛的故事
|
九块钱环游世界·第11个故事 背着双肩包从学校出发, 先坐22路公交车,五块钱,再坐77路公交车,两块钱。 下车,搭江培伯伯的渡船过江,两块钱。 一共九块钱,就能到达我最初热爱的麻风康复村——泗安岛。 后来,去的村子越来越远,认识的老人家也越来越多。 或许你也想了解他们, 就此细碎地记下每次见面的小小故事。 01 危险 大衾岛,也叫大襟岛,是江门台山赤溪镇的一个海岛。医院,是专门隔医院。大衾岛离开陆地有14海里远,90年代以前,医院的大木船。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在这个麻风岛上发生。医院修建于民国十三年,也就是年。吴院长是医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他是年1月来到医院当医生的。刚来的时候,岛上只有6、7位医生,要照顾近个病人,就连病人的截肢手术都由医生在岛上做。医院的一条大船,那时医生一个月有4天假期,自己安排几时放假、几时上班。运药运米都是这条船,光是病人吃的大米一个月就需要运几十担。有一个冬天的夜晚,吴院长要跟船进岛去。冬天大多是晚上才开船,因为晚上水位比较高,水位太低的话船没办法靠岸。天很黑,他在船头有些冷,打算走进船舱避一避风。一进去,出大事了!海水漫进了整个船舱!吴院长马上大喊:“不行了!进水了!”吴院长还记得,他看见那几十担大米都泡在海水里。这条船已经很老很老了,不知是哪处的木头裂开了缝。开船的人一听,立马调转船头,开足马力飞驰回去。那时候船已经在大海之上了,要是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刚回到码头,船就沉了下去。这是发生在年的事情。02 信仰 有一位澳门的陆神父,是天主教的。陆神父去过广东、云南、四川很多地方的麻风村,也知道了大衾岛上有个麻风村。一开始,神父一个月来一两次,每次都会带一批礼物来。吴院长还记得,有一次神父买来一只烧猪,可惜那天风浪太大,等了很久都没法开船,神父只好离开。年,陆神父问吴院长:“我能不能安排4个修女来照顾他们?”这时候的麻风病人绝大多数已经治好,他们已经是康复者了,当时他们面临的更多是麻风后遗症所造成的截肢和神经痛带来的不便,以及年纪渐老带来的病痛的困扰。吴院长做了很多努力,终于申请到当地的同意。四位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三位是印度的,一位是西班牙的,就在这个海岛上帮助了老人整整十年时间。神父又出钱修了个饭堂,老人们不再需要用自己残疾的手劈柴做饭了;又买了两台发电机,和一个自来水塔。老人的生活费神父也补贴一些,后来又把老房子全部装修一遍。修女们年离开了这个岛。院长说,“神父老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到处‘乞钱’了。乞不到钱,修女也没办法,只好走了。”陆神父出生在年,这时候已经94岁,比大衾岛上很多老人家还要老。03 张醒南 以前岛上有个病人,叫张醒南。张醒南是吴院长的得力帮手,很能干——他是岛上的赤脚医生,医生不在的时候,有人生病可以找他;他还负责开公家的小船,经常出去赤溪镇,帮病人买东西回来。有一年岛上干旱,他想办法带人上山修了一条水路,引水下山。文化大革命时期,张醒南得了血吸虫病,院长带他出岛,找岛外的医生给他治病,不敢提到麻风病,就谎称他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张醒南,也就是德妹婆婆故事里的男主角。德妹婆婆温和寡言,那时候在做病房的护理,还有负责帮药房煲药。医院在病区隔壁的一栋楼给他们安排了个房间,也就是同意了让他们住在一起。两个人住在这儿,准备登记结婚,条件只有一个——可以结婚,可是不能生小孩子。那时候,麻风康复者是不允许有后代的。可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一直也没去登记。后来,年,58岁的张醒南大出血去世。△在这栋楼的二楼给他们安排了个房间04 寻亲 病人来到这个岛上隔离治疗,他们有的可以跟亲人写信联系,有人已经被亲人抛弃,有人灰心丧气,主动跟外界断绝联系。有一年,一位年轻人找上岛来,他来找他那失去联系好多年的叔叔。说出名字,院长告诉他:“你的叔叔已经死了。”侄子不放弃:“死了我也要去墓地看一下。”麻风岛上是一个微型社会,病人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亡,在这里火化,在这里埋葬。从病区出发,走过一条小路和一条小桥就是墓地了,离开的人都被埋葬在这里。院长请一个病人带他去找。想想又说:“可是不知道你叔叔走之前,有没有交代别人帮他做牌子。”在这里,人走了没有墓碑,一个牌子写上字就是他们的墓碑。带路的病人正好是叔叔生前的好朋友,他说:“做了,我帮他写好名字的!”侄子很感激,给这位病人块钱表示感谢。岛上有个病人开的小卖部,侄子买了好多香烛和元宝,到坟前烧给叔叔,烧完才肯离开。05 不舍 岛上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听说有一个阿婆,好像是海南人,她的手脚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脸也干干净净,不像个得过麻风病的人。阿婆的儿子是暨南大学毕业的,儿子夫妇两人每年都来看她一次。后来,阿婆去世了。儿子来了,带来一个装骨灰的罐子和一个纸箱,要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火化室的机器总是点不着火,试来试去,一点没有办法。院长沉思一会儿,让这位儿子到小卖部买两串鞭炮回来。果然,鞭炮一点,火就烧起来了。院长感慨道,可能是这位妈妈不舍得离开。06 亲人 阿啟入院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儿子,和一个四五岁的女儿。孩子的妈妈早已去世,阿啟入院,家里就只留下两个小孩子相依为命。儿子婚前一直还有跟阿啟通信,结婚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阿啟请院长开车带他回家去找,才知道儿子已经搬去广州,女儿也已经嫁人。村民说:“我这里有你女儿嫁去的地址,你要吗?”院长带阿啟来到斗山镇,找到了地址上的村子。院长让阿啟先不要下车,他有一条腿是瘸的,下车会引人注意。院长找到阿啟的女儿,上前去问:“xxx,是不是你?你爸爸来了,你愿不愿意见?”阿啟见到女儿,一直一直哭。女儿有解不开的心结,她无动于衷,冷冷地说:“我也没有钱,我没钱给你的。”07 “亲人” 今年秋天,我跟汉达协会还有退休的吴院长一起上了一趟大衾岛。年,医院宣布关闭,医院的44位麻风康复老人搬迁医院。从年到年,医院完成了它87年的使命,总共收治过位病人。现在,岛上只剩下少数打渔为生的渔民。大衾岛中间有一座山头,北边是医院,是麻风村;南边住着渔民,名为南湾村。我看见有一位阿姨在地里种番薯苗,于是过去搭话。阿姨姓钟,叫阿彩,也是这里的渔民,医院这边空置了,她就经常过来这边地里种些东西。聊到搬走的老人们,阿姨问:“黄少宽是生还是死啊?”黄少宽婆婆今年90多岁了,医院以后,生活得十分精彩。我把黄少宽婆婆的近况跟阿姨说,阿姨告诉我:“哦,我二妹妹认了黄少宽做契姐(干姐姐)的呢。”阿姨说,以前他们渔民村很多人都认麻风病人做契爷、契妈(干爹、干妈)的,跟他们接触很多,平时过年过节也会做糍粑送过去。在当地的习俗里,认亲是迷信中长辈要替晚辈挡灾挡难的意思。病人们才不怕,还有什么比得麻风病更可怕的呢?反而,认一个亲人,心里的寂寞被消解了,被人挂念着,也有个慰藉。老人们搬离医院的时候,这些截肢的、瘸腿的、拄拐杖的、走不动的老人家,要通过一段石滩路才能上船离开。那时候渔民村的男人好多都来了,老人家走不了,男人就把他们背上船去。08 南湾村 其实现在,年轻的渔民大多已经离开了,岛上只剩下年老的渔民。医院搬走以后,医院的热水器、楼梯栏杆、电线都拆去卖了,能换钱的都拿去换钱了。以前的医疗室、老人住过的房间,就用来存放东西。进岛这天,正好遇见一个驼背的老阿婆。阿婆看见吴院长,惊喜地打招呼:“你怎么来了?”院长马上很懊恼的样子:“哎呀,没买点东西来给你!”吴院长介绍说,这位老阿婆是以前南湾村的接生婆,现在两个儿子都出去外面打工,岛上就只剩她和丈夫两个老人家自己生活。阿婆说:“你来看我就很开心了!早知道你来,我就留点虾蟹给你带回去。”吴院长从钱包抽出块钱,非要塞给阿婆。阿婆不肯要:“不用了阿叔!不用了阿叔!”最后还是推不掉,低着头自言自语:“唉,阿叔你怎么这么好心……”吴院长说起当年的生活。南湾村的村民以前生活得困难,有人生病了,就翻山过来求这边的医生帮忙看。吴院长那时候最年轻,于是就经常是他跟着过去。这座山,渔民走过来要八个字(40分钟),医生走得慢,需要花一个小时。有时,医院的木船要出去,好多渔民就翻山过来,医院的船出去陆地……这个海岛离陆地好远好远,小小的地方,医生、渔民、病人就在这里互相帮助,互相照应。09 九年后 医院搬走以后,这里的宿舍就没人住了。当年基督教修建的西式建筑的半圆拱顶上,一只一只带美丽花纹的大蜘蛛在这里织网觅食。现在,大衾岛已经是台山核电站的散热区,也有人周末带上鱼竿到这儿沙滩边上钓鱼。我在岛外看见一个租赁店名为“大衾岛钓具店”,大衾岛就是一个岛,没有麻风岛的含义。吴院长带我们租了一条快艇进岛,担心不好靠岸,还提前计算好涨潮退潮的时间。退休十年了,他对这里依然非常熟悉。快到大衾岛的时候,吴院长提醒开船的人说:“绕开这里绕开这里,这里水下面有块石头!”不过,开船的人还是碰过去了,果然小小撞了一下船底。吴院长对这里太熟悉了,在岛上做医生的时候,这片水域他走过无数遍。△吴院长重访大衾岛谢翠屏儿互相激励呀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ngyaozia.com/hyzxw/6937.html
- 上一篇文章: 本地ldquo最美女儿rdqu
- 下一篇文章: 江伯欠我一盒廖记棒棒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