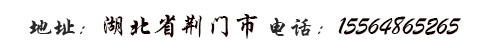深度个麻风点现状好吗透过石屏村
|
北京皮肤病专治医院 http://m.39.net/pf/a_7239999.html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免费查治麻风患者约50万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以人口为基数,麻风新发病人在十万分之一以下,就达到基本消除水平。中国的麻风新发病例早已远远低于这个标准,且新发病例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近几年连续年均不到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山石屏村,年被设定为麻风村,是我国现存的所麻风院/村之一。近日,记者跟随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救助项目组,走进这个村庄,看到了在那里发生的改变、孕育的希望。 麻风村的老人在下象棋。杨金伟摄。 火把节摆开长桌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集少、边、山、穷特征为一体,全省16个州(市)均曾有麻风流行,洱源县是历史上麻风高流行地区。山石屏村背靠罗坪山,面朝黑潓江。白日里蓝天白云,黑夜宁静得只能听见鸟叫虫鸣,宛若一处世外桃源。也正是因为山水阻隔、人迹罕至,山石屏村年被设定为麻风村,集中收治麻风病人。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副会长、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杨军介绍,山石屏村的前身是年成立的洱源县山石屏麻风院。当时,这里没有房屋,没有耕地,没有道路,多名麻风患者生活在方圆5公里的山沟里,条件十分艰苦。60多年来,这里共收住洱源、大理、丽江、兰坪、剑川等地麻风患者人,至年患者全部治愈。年1月8日正式更名山石屏村,摘掉了麻风村的帽子,目前住院疗养康复者还有44人。农历六月二十五(今年的7月27日),是白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为了迎接这个重要的节日,山石屏村的麻风康复者前一天早早地开始了筹备工作。男人们伐木、砍柴,女人们上山采摘木耳、菌子和野菜。制作大火把,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大火把由一根长约15米的松树作主干,主干的中间穿插12层木柴,每一层代表一个月,木柴的缝隙插满各色小旗子、苹果、梨和馒头等。主干的顶端架着两个四色彩斗,按照风俗,村里德高望重的人要在彩斗上题字,而今年的题字人是洱源县疾控中心名誉主任李桂科。他一手拿着毛笔,一手端着墨汁,一笔一画地在彩斗上写下“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一、二、三,往上拉!”由于没有吊车,村民们从3个方向将大火把拉起来,竖立在空地的中间。点燃火把前,村子里摆开了由33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救助项目组工作人员、企业家代表、志愿者代表、媒体人士,与山石屏村麻风康复者及其家属一起就餐,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今天,我们以长桌宴这个云贵地区少数民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谢谢长期以来关心爱护麻风康复者的各界人士。”李桂科端起酒杯,分外高兴。山石屏村邻村村民邓阿姨给大家带来了上山采来的菌子和野菜,而在以前,邻村人都“不愿意靠近这个村子,更别说一起吃饭了”。夜幕降临,火把节的重头戏来了。李桂科举起竹竿点燃火把,火苗蹿成烈火,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村民们围着火把,载歌载舞。火越烧越旺,插在火把上的小旗子、苹果纷纷掉落。村民们抢着去捡,捡到苹果就吃掉,寓意来年不得病;捡到小旗子就拿回家插在门框上,预示着好运到来。听余正华讲往事 火把熄灭,庆祝活动结束了,村子恢复了宁静。麻风康复者余正华被人搀扶着回到房间,打开半导体,听上了白族小调。今年77岁的余正华,年来到山石屏村。年,原卫生部制定的《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明确了麻风病“积极防治,控制感染”的原则,提出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防治措施。同年,全国范围的麻风大普查展开,交通不便的深山或海岛上开始修建数百家麻风院,大规模收治麻风患者。患上麻风的余正华收拾了行囊,自行来到这里。说起几时发病,余正华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起初只是眉毛脱落,后来手指勾起、脚部溃烂。记者看到,老人的鞋子中间有一条明显的折痕,鞋的前半部分是空的。“‘好’人都变‘坏’咯。”余正华说。比身上的创伤更刺痛人的,是外界的歧视与偏见。有一次,余正华到江边洗衣服,江对岸传来一阵喊叫。“不能在这里洗!”原来,余正华在江上游洗衣服,邻村村民担心“水流下来传染下游的村子”。有时,邻村村民放牛路过山石屏村,会把牛鼻子抬得很高,“不让牛吃到这个村子的草”。几十年前发生的这些事,余正华仍然记在心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玉文介绍,我国现有麻风院/村所,麻风治愈者20万人。其中,10万人有可见的残疾,70%的麻风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自年开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对全国的麻风院/村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在国家政策和财政的支持下,麻风康复者群体的生存状况已有所改善,但在一些偏远山区,基本生活和康复医疗仍得不到保障,歧视现象仍然严重。“很多时候,歧视是因为不了解。”杨军说,“麻风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95%的人具备抵抗能力,即使接触麻风病人,也不会被感染。只有营养不良、抵抗力差,与麻风病人长期近距离接触的人,才有被感染的可能。而且,麻风不是遗传性疾病,治愈后的麻风病人没有任何传染性。”刘玉文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了“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救助项目,向社会倡导“麻风不惧阳光同行”的公益理念,同时对全国现有的麻风院/村开展救助。此外,项目会进一步推动将麻风康复者列入残疾人类别,为其办理残疾人证,探讨由残联系统、疾控中心共同参与的麻风康复者管理模式。建一座通往外界的桥 山石屏村之所以可以脱掉麻风村的帽子,与李桂科有着莫大的关系。李桂科是山石屏村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一位从事麻风防治工作38年的“老麻医”。“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山石屏村。”李桂科记忆犹新。当时,23岁的他刚被洱源县卫生防疫站招录,与另外5名同事一起来到了山石屏村,从事麻风防治工作。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受到震撼:土坯房破旧不堪,病人衣衫褴褛、眉毛脱落,有的面目狰狞,有的手指、脚趾甚至肢体缺失。“当时,我们穿隔离服、雨靴,戴口罩、手套,全副武装以防感染。可是心里还是没底,因为药物的效果不明显,我们也不相信麻风能治好。”事情有了转机。年4月26日,李桂科给村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北京的专家在西双版纳做的麻风联合化疗很成功,县里也要引进开展。”李桂科和县疾控中心的11名同事对全县麻风患者进行清理复检,年下半年开始在县里推广联合化疗。到年年底,洱源县发现的麻风患者全部治愈。李桂科的使命似乎完成了,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为了方便说话,李桂科总想离村民近一些,可他每走近一步,村民就退后一步,总是保持一段距离。“虽然他们的病治好了,但仍然没有走进社会。”山石屏村与外界之间被黑潓江阻隔,只能靠船摆渡。年中秋节,16名村民去河对岸拉玉米。黑潓江水流湍急,船刚刚离岸就翻了,夺去了6个人的生命。“村民们拄着拐杖站在江边,依依不舍目送我的情景始终印刻在我心里。他们需要我!”麻风康复者本就饱受外界歧视和偏见,而蜿蜒而过的黑潓江,又无情地将他们隔离在山谷里。这场灾难让李桂科痛下决心打破这种隔离,为村民们修建一座通往外界的桥梁。修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桂科搬进村子,与麻风康复者同吃同住,抓紧筹措修桥资金。山石屏村后山上的松树可以砍伐能造纸,村民们全体出动。年春天,一座横跨黑潓江的铁索桥建了起来,村民第一次走出隔离区。“太阳一出来,村民们就会走过桥,到对面晒太阳。”李桂科笑着说。在李桂科的努力下,先后有多名志愿者跨过黑潓江,走进山石屏村,为麻风康复者提供心理服务,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年6月,山石屏村的老人集体去大理旅游。“老人们特别兴奋,看见楼房非常惊讶,对着窗户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层楼好高啊’。”广东汉达康福协会志愿者曾庭梅回忆道。如今,老人们不再艳羡外面的世界,村子焕然一新,建起了二层小楼。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苦日子已经过去了。”每天和邻居们聊聊家常一下下象棋,余正华现在过得很舒心。垛木房成了博物馆 麻风康复者和家属现在的居住区是一栋颇具白族风格的二层小楼,掩映在苍翠的树木之中,院子里鸟语花香。每位麻风康复者都有自己的房间,房间基本是两卧一厅一卫一厨,家具和生活用具一应俱全。从居住区侧门出来,沿着一条蜿蜒于鲜花丛中的山间小径上坡,还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垛木房,那是过去麻风患者的居住区。垛木房的外墙由一根根圆木垒起来,每间房住两三个人,有的房子被布帘隔成5间,要住10个人。“当时没有电,要用煤油灯,生火做饭也是在房子里。墙和屋顶都熏黑了。”余正华说。如今,垛木房成为了麻风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区,陈列着麻风康复者自己动手制作的各种生活用具。马掌、锄头和方铁斗勾勒出了几十年前修路的情景。麻风康复者宋文红介绍,渡过黑潓江后,山石屏村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运送物资都是靠人背马驮翻山越岭。年,李桂科带领村民开始修路。每个村民一有空闲,就会拉着马上船,摆渡到对岸挖土运土。就这样,村民们一个锄头一个锄头挖通了一条路。“建博物馆就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李桂科介绍,博物馆分为3个展区,第一个展区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主要以实物形式展示当时村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二展区是一栋原貌复建的6间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人居住的垛木房,展示当时麻风病人的生活状况,以及麻风病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的生产状况等;三展区是原状修复的医务室,展示麻风院发展以及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老照片。博物馆里陈列的很多珍贵照片是李桂科拍摄的,为此他已用坏了6台相机。“这些点点滴滴,反映出了麻风康复者尊重生命、热爱生活的态度。”刘玉文表示,山石屏村麻风历史博物馆以最朴实生动的形式展现了跨越60多年的麻风村历史变迁,是全国麻风防治成效的一个缩影,将成为人们了解麻风历史、科普麻风知识的重要阵地。他呼吁全社会都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ngyaozia.com/hyzzz/6805.html
- 上一篇文章: 在农村,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杂草,无论是房
- 下一篇文章: 味中药功效及主治总结画重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