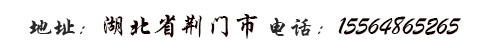有故事的男同学这个龙舟男孩刷新浙大
|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刘俏言 “梆、梆、梆”——鼓点声越来越急促,身体前倾,把桨深深插入水中,再用力一划,一声鼓一声桨。3月的海南天气还不热,但汗珠顺着杨小和的脸淌进粉色的队服里,央视转播的画外音将镜头对准他们的龙舟——“第5赛道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学生们……” 杨小和听不见,鼓声就是号令,他是领桨手,在年中华龙舟大赛青少年组米决赛上,他只想赢。 中华龙舟大赛央视转播杨小和参赛画面 26.秒!用0.秒的差距,杨小和带领的浙江大学龙舟队拿下第三名,龙舟队的队员们紧紧相拥,庆祝着有史以来最棒的成绩。 后来,杨小和时常回忆起这个大二的春天,海南的风是凉的,港北港的水有咸味,央视镜头前的他意气风发,手中的龙头奖杯反射着漂亮的光。 中华龙舟大赛比赛现场(粉色队服为浙大队) 奖杯、奖状、还有队长袖标包着的一大包参赛证,正在被杨小和打包,一一装纸箱,如同六月的杭州,梅季后的高温猝不及防,他毕业了。 杨小和的奖牌 杨小和的奖牌 毕业季,是没有长辈见证的毕业典礼、没能凑齐所有人的毕业合照。和被疫情占据三年的青春告别,总带着些遗憾和不舍。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杨小和决定和龙舟队的伙伴们在校园的启真湖上再划一次龙舟,给那些疯狂过的日子,一场最后的仪式。 “分的二课分,30次比赛,59个单项,或许是目前浙大最高的记录,这是我本科留下的足迹。从今往后,揣着这些回忆奔赴下一段路途,总会发现新的美好。”杨小和说。 “小太阳”和浙大龙舟队 码头上,一个人在启真湖上划10公里龙舟的事儿被提起,教练翟旺旺说杨小和绝对是因为感情问题才这么自虐,杨小和不承认,说这是给自己“加训”。毕业让这群散落在各个校区的水上俱乐部学生难得又聚到了一起。指导老师许亚萍让他们珍惜这唯一一次不用穿救生衣就能上码头拍照的机会。 龙舟队的毕业照,一排左为杨小和 杨小和从仓库把龙舟的头和尾都扛到了码头上,还找到了自己的“专用桨”,上面有一个漂亮的红色标志。他摩挲着桨的底部,用掌心给它擦了个锃亮。拍毕业合照的时候,他左手提着龙头,右手拿着船桨,姿势有点中二,对着镜头拼命笑。 合照的这群人里,和杨小和一起参加过比赛的不少,不过一起参加中华龙舟大赛的老队友都毕业的毕业,离开的离开了。杨小和试图到仓库里找他们当年训练时用的“小太阳”,没找到。 年中华龙舟大赛浙大龙舟队合影 那是年大年初六陪伴杨小和与队友们集训的神器,3月就要比赛,2月,龙舟队的学生们自发返校集训,他们有的在玉泉校区读物理和数控专业、有的在西溪校区读心理、最远的队员在舟山校区海洋学院,索性他直接住在了紫金港学生宿舍的阁楼里,没落下任何一场训练。 训练时天天下雨,衣服不敢穿棉的,被水浸湿会更冷,练的时候一身汗,混着雨水,上岸风一吹就一个哆嗦,10个男队员和1个女鼓手1个舵手,还有若干其他队友挤在一起,围着仓库里的“小太阳”取暖,没等把自己烘干,就要继续下水进行下一个五公里训练。 大学期间参加了那么多场比赛,唯独年的中华龙舟大赛给杨小和印象最深。倒不是因为训练苦,是曾在电视上看过中华龙舟大赛,既好奇又羡慕。那时候他还在烟台老家读初中,是个斤的小胖子,没见过龙舟长什么样,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参赛,还能成为第一排的领桨手。鼓手坐在离他不到1米的龙舟头上,高举鼓棒,“梆、梆、梆”,敲一下,他就用力划一下桨,那是信任的声音。 杨小和信任队友,更信任自己。这种自信无关天赋,是高中在寝室里拽着上铺床围栏做引体向上,是高考之后沿着烟台的海边背40斤的书负重跑,是卧推重量从60斤增至斤,肌肉填满手臂的踏实。总之杨小和不是小胖子了,他想成为一名医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对比了多所学校的医学院,还是因为浙大能划龙舟,选择来杭州读书。 龙舟队有早训,五点半起床集训完毕后回寝室换衣服,刚好能赶得上八点的第一堂早课。这样的作息几乎贯穿着杨小和前三年的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生活,好在有无数场竞技等着他,给枯燥训练的日子一点儿盼头。 “队旗”和那些比赛中的青春 奖杯、奖状和各国队旗 码头旁的办公室里,一面架子上都是奖杯和奖状。还有用透明胶粘在架子前的队旗。清华、北大、同济、辅仁还有哈佛大学。高校水上项目有个传统,就是在比赛后交换队旗,这些队旗里,一大半都是杨小和去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交换来的。 年的夏天是可以一张机票就飞到匈牙利的夏天,杨小和整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在水上晒太阳和落水之间反复横跳,翻船是常态,他甚至不记得落水有没有上百次了,落水的第一时间得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别掉水里,人一定没事,但传言启真湖底已经有上百副眼镜了。他在学校训了一个月,又跑到千岛湖训了一周,为的是匈牙利索尔诺克世界大学生皮划艇锦标赛,别的学生都是专业的运动员,就杨小和是业余的。他老是不愿意回忆这段尴尬的经历,“训了这么久,到那里非常丢人拿了个倒数第二,还算是超常发挥了。“他说。 记忆中的匈牙利之行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杨小和的队服是粉色的,在交换队服的环节深受外国人的喜欢,甚至造成了哄抢的局面。比完赛和对手们坐电梯,香水味混合着汗水味充斥在这个空间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加拿大的运动员可以运动学习两不误,退役之后还能接着当NASA的工程师,还有初次尝试的三分熟的牛排,全吃光了。 匈牙利比赛现场(右三为杨小和) 在匈牙利比赛后,杨小和举着国旗合影留念 如果把年到年杨小和的参赛轨迹在地图上连线,就会发现只要有水的地方他都去过了,在西溪湿地上划皮划艇马拉松、在黄河上划龙舟、在青岛的海上玩帆船——贵州、海南、浙江、陕西,他上过奔跑吧和跑男团划过龙舟、甚至连五大连池也去了,参加的是冰上龙舟的比赛。每参加一场比赛,就拿一张奖状和奖牌,快进画面,便是一页PPT也写不下的获奖履历和沉重的奖牌。 在浙大,本科毕业生的第二课堂分数只要4分就可以顺利毕业,得益于这些比赛加分,杨小和的分数是分,在网站上显示,这是浙大历史以来的最高分数。 杨小和的二课分创下了浙大历史新高 年的12月,杨小和看到福建有一场成人皮划艇比赛,鬼使神差地,他一个人偷偷报了名,没告诉任何人。他在码头借了一双桨和救生衣,背着包就去了福建,比完赛,高铁已经赶不上了,他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又早起上课去了。 杨小和一人跑去福建参加比赛 那时的杨小和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省参加比赛了。之后,新冠肺炎疫情悄然而至,龙舟赛被大面积取消、出省参赛变得尤为困难,而一张机票到国外比赛,仿佛已经是遥远的、上个年代的故事。 潮水袭来,年的一道闪电,将杨小和5年的学医生涯劈成了两半,搬校区、上网课,去医院见习实习、考研,书本将他的生活填满,他拿起笔,放下了船桨。 “蓝码”和被取消的比赛 “你们现在训练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码头上,拍完毕业照的杨小和在跟下一届的学弟学妹聊天,他们是20级的学生,踏着疫情入校,并加入了杨小和曾经所在的水上俱乐部。 “现在的训练要打卡了,我们除了校内的三好杯,就没再参加过比赛了。”听到学弟的回答,杨小和叹了口气,又想起自己在年的端午节执拗于在紫金港的启真湖划龙舟的仪式感。那个被困在家里的上半年,史密斯机卧推,卧拉,器械划船,引体向上,倒立撑,每天都坚持做,他总觉得疫情很快就会过去,自己摩拳擦掌,等待着下一场比赛的到来。 然而回校后,迎接他的不是龙舟比赛,而是20几场考试。医学生原本的考试就多,疫情无法回校,积攒下的考试就更多了。他也从紫金港校区搬走了,去了华家池校区,那里没有码头,没有龙舟,在这个校区的学生都是医学生,校园里的学生们步履匆匆,不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小和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杨小和在耳鼻喉科见习 杨小和被分派到了浙大二院见习实习,他是最早一批两天一次做核酸的人。医院对疫情防控的要求更高,出省变成了一件不可奢望的事情。不过他也没有理由再出省了,中华龙舟大赛定格在了年,疫情之后便再也没有举办过,其余的赛事也在陆续取消。 进手术室,值大夜班,见识生命的脆弱,也目睹过真正的生离死别。第一次看到没有救治希望的病人,他的女儿一个人蹲在走廊痛哭,那是成年人崩溃的瞬间,在分娩室值班,他听过孕妇彻夜撕心裂肺的哭喊。高度紧绷的神经挨到了回校园的那一刻,紧接着被保安要求出示蓝码。 疫情期间,校园要刷蓝码,每天打卡才能保住蓝码。准备考研、高强度见习实习,就在某个因为忘记打卡在校门口等待申请新蓝码的瞬间,杨小和的情绪突然有些失控,他想把这一切归结于“该死的疫情”,却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感。 “那时候但凡有点不顺的事儿,就觉得都怪疫情。”他说。 浙大紫金港校区亮起灿若星辰灯 年的11月末,浙大紫金港校区发现了一例阳性病例,夜晚,灿若星辰灯彻夜亮起,学生全员做核酸。这场疫情也波及到了华家池校区,杨小和的两个室友在实习路上成了黄码,回寝室收拾了行李,就去了校内的华凯酒店,进行3+11天的隔离。 学生全员做核酸 于是没有被隔离的杨小和肩负起了帮室友取外卖的重任,从校门口送到酒店,再交给防疫人员消毒,送到室友手上。一名室友每天都要喝咖啡“续命”,另一名室友觉得隔离餐的肉吃起来还不够爽,盒马鲜生点了夫妻肺片和酱牛肉,就着果酒给自己加餐,没过几天就胖了,嚷嚷着让杨小和送瑜伽垫,要健身减肥。 “马拉松”和疫情的三年 杨小和站在滑板上,手里是一支被他划断了的废桨,用这跟桨撑着地,一点点往前滑,这是他自创的陆地模拟划船法,在没有比赛也无法回紫金港训练的日子里,他靠这种方式,寻找一种划船的感觉。 年末的那场跨年夜,杨小和得空医院出来,和中华龙舟大赛的队友们在浙大舟山校区聚了聚,他们已经两年没碰过龙舟了,但还是下意识地比谁的划船机拉得更有力,按照浙大的惯例,跨年夜的那天,学校会给全校的学生发烤全羊,杨小和领了一份,不太好吃。 曾经那个在赛场上意气风发的少年正在加速成长,比赛时,只要几十秒,就能分出胜负,他沉迷于荷尔蒙迸发的那一个个瞬间。而学医之路漫长,五年本科之后是三年的硕士规培,然后是博士,医院,也永远会有下一个病人,杨小和似乎永远都无法说出自己已经赢了,就像这没完没了的疫情,他开始习惯马拉松式的奔跑方式,给自己设置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并努力实现它。 第一个目标是考研上岸,他选了运动医学方向,和他同台竞技的很多是考研“二战”甚至“三战”的学生,他的战场转移了,医院见习时抽空在示教室背书,晚上在自习教室里刷题。 示教室杨小和的座位上都是考研的学习资料 他依然会珍惜参加比赛的机会,划马拉松,最远的一场在湖州,单人皮划艇21公里,最近就在杭州大运河,双人皮划艇马拉松16公里。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不再固执地要拿第一,而是“有的玩就行”,如果有队友在身边就更好了,比一次少一次,即便是小比赛,只要在省内,杨小和都会争取参加。 如今,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考研上岸的第二天,杨小和回到紫金港校区,又一次拿起船桨,启真湖的湖水那股味道没变,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他仰头,任凭阳光晒在他的脸和脖子上,一个人,一条小龙舟,船底的积水打湿了他的鞋袜,过往比赛的一幕幕在脑中开启自动回放——“那些比赛将是我大学最美的回忆,永远都是。”他对自己说。 “你们即便毕业了,想回学校划船,也成,跟教练打个招呼就行,浙大永远欢迎你。”指导老师许亚萍在码头上说着对毕业生们的嘱托,把杨小和从回忆里拉进了现实。他毕业了,拍毕业照的这一天,杭州出梅了,阳光照在启真湖的湖面上,波光粼粼,杨小和第一次穿着学士服划了趟龙舟。 喊着他们熟悉的口号,学士服的袖口被打湿了 “浙大!”“龙舟!”“走嘞!”“诶呀!”喊着他们熟悉的口号,学士服的袖口被打湿了,杨小和的动作还是那么标准。他盘算着,这是他十年之内最后一个暑假了,该早点回家多陪陪父母,该去海边冲个浪,该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做一个快乐的,届毕业生。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ngyaozia.com/hyzxw/11500.html
- 上一篇文章: 本草纲目中记载,马齿苋能治11种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